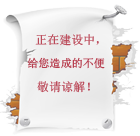很久之前,与我们通信的一个人问我像good―better和go―went这样的不规则形式是怎么产生的。他不仅清楚这个问题的语言学特质,也知道关于这种现象的术语,即“异干互补” (suppletion)。即便说最简单的英文句子时也会遇到异干互补的情况。想想动词be的变位形式:am, is, are。为什么会区别那么大呢?为什么mad比较级是madder, rude是ruder,可是bad却是worse, good是better? 收到这样的问题,我意识到就算我能列出一打语种中异干互补形式的清单,并且知道它们中一部分的词源,我还是没法就此给出一般性解释。我翻阅了大量关于印欧语历史的书籍和各种各样的序言,惊奇地发现他们全部都只枚举了这些形式而没有说明它们出现的时间。我也向很多同行求助,但依然没搞明白。我把这个问题暂时搁一边,但心里始终惦记着。有一天,在给著作填充没完没了的参考书目和粗略翻阅《Glotta》杂志(专注希腊拉丁语文学)时,我找到一篇探讨古典希腊语的异干互补现象的好文章。当然,文章中提到了之前的相关研究成果。我顺藤摸瓜深入了解,现在可以谈下异干互补这个问题了。
这段介绍对读者们而言或许多余,但我写它是想说明两件事。第一,有时解答一个貌似不咋样的问题老折腾了。第二,这个插曲可以警醒我们。这本探讨异干互补来源的主要著作是一本百年前的"著名"的书,在它之前还有很多重要的先行者。就像很多研究者说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它。不过,显然,这本书并不是名震天下,许多历史语言学老学究折腾了好多年也不知道它。这远不是一个来自学生、朋友或读者的刺破个人自负的问题!好了,进入正题。
语法和构词都有规则形式。比如,很多语种都会用一个特殊后缀通过阳性词汇构造对应的阴性词汇。因此,德语Freund(男性朋友)对应Freundin(女性朋友)。英语从法语中借来后缀-ess; 因此有了actor~actress, lion~lioness,诸如等等。但在任何一种语言中,表示“女孩”与“女人”的词都不是衍生自表示“男孩”与“男人”的词。德语和意大利语已分别承认Professorin(女教师)和Professoressa(女教师),但在英语中并没有professoress,尽管我们有相当多的女性教员。Man and woman, boy and girl形成自然配对(它们的所指形成自然配偶);不过在语言中彼此是分开的,人们也没觉得这样不妥。

这是叶夫根尼・扎米亚京――小说《我们》的作者的肖像。他在20世纪20年代便已指出当We变成I的复数时发生了什么。
语法服从思维并将不同的形式统一。它让我们觉得work, works, worked和working归到一起的。英语几乎没剩多少曲折变化,但从拉丁语与希腊语的词汇变位总结中便足以了解有多少词汇形式是可以归到一起的。我们只能向回推导并一直回避这个问题?为什么有man和woman这两种分开的形式?因为这一对儿中的每一个都被觉得是独一无二的,而非衍生出的。何以见得?因为事实就是这俩单词不同。这解释明显是个恶性循环。我们没法确定为什么思维在合并某些事物的同时将别的事物分离。不过,某些情况还是可以解释的。比如,horses是horse的复数(one horse/many horses),但I 却不能被复数化,尽管语法告诉我们we是I的复数。因此,we和I有不同的词根挺正常。同样的,they也不是he,she, 和it的复数。
早期印欧语人创造了表示"first"和"second"的词,把前者理解成“最初的一个”和“接下来的一个”,并且没看到"first"和"second"与"one"和"two" (我们今天分别称之为序数词和基数词)的内在关联。One/first与two/second这两对异干互补形式在很多语言中都出现,带有罕见的一致性。我们好奇为什么good的比较级是better。我们应该先问自己better的比较级原形是什么。它压根就不存在。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better大概意味着“提升的,补救的,弥补的”。Good需要一个伙伴来表示“比good更好”,而better承担了这一职责。我们可能更喜欢"gooder",但我们不屈不挠的祖先选择了避易就难。整个印欧人世界的情况都是如此(跟拉丁语的bonus/melior/optimus相比,better和best还有点相似,谢天谢地吧)。Worse很可能表示“被缠住”。然而better后缀-er(它曾经也存在于worse中)指明这两个形容词的比较级职能都不是隐蔽的。
可能最棘手的情况就是动词的异干互补。我们到处都能遇到像go/went这样的例子。此外,现在时同过去时一样经常被影响。在拉丁语中,go的不定式是andare,但I go是vado。法语中这一对儿是aller和vais。总览整个印欧语体系,这种异干互补形式出现在"come; go", "eat", "give", "take, bring, carry, lead" (那些稍微学过拉丁语的人一开始都会撞上fero/tuli/latum), "say, speak", "strike, hit", "see, show", 当然还有"be, become"等等这些动词之中。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相关形式是独立的(就像andare和aller),换言之,各语种创造而非继承了异干互补形式。英语的情况尤为戏剧化,古英语中gan"go"的过去时是eode,该词衍生自另一词根。在中古英语中,went,本来是wend(比如wend one's way)的历史过去式,取代了eode。英语本来有机会产生gan的常规过去式,但是却决定用一个异干互补来代替另一个异干互补。甚至在精心编辑的哥特语《圣经》(14世纪时从希腊语翻译)中,过去式gaggida (来自gaggan; 将gg 读作ng)也出现了一次。这是在哥特语中,英语没有。那些懂德语的人会觉得gehen/ging"go/went"是相关的,但实际上不是。这种错觉源于首辅音g-。
关于这个现象没有一个完全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有些事实值得说下。早期印欧语并没有我们觉得理所当有的一些时态。一个经典例子是日耳曼语缺少将来时。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即便在今天,没有将来时有时也没关系。上下语境就够用了。
比较一下:I am leaving tomorrow and If I leave tomorrow…过去时和完成时的差别也可以很模糊:"Did you put the butter in the refrigerator?"或者"Have you put the butter in the refrigerator?"这差别无关紧要。任何说英语的人也不会悲叹英语没有不定过去时。几世纪以前,动词常常以它们是表示持续性动作还是短暂(结束)性动作来分类。有时,像see(持续性)和look(短暂性)这样的动词后来便合并成到一个范式中。比如"go, walk",与之差异较大的是"reach one's destination"。想想speak和say的区别。这可能就是went与go成为搭档的原因。Eode词源不明,至于它的内在形式,对5世纪的人和我们来说都没啥意义。
范式内部的同义词合并可能不是异干互补的唯一来源,但是它的一个重要来源。可能最令人着迷的问题是,为什么语言选择同样的动词和形容词来藐视规则语法。似乎目标都集中于那些最常见的词"good; bad," "be; come; go; take; eat; speak"或是类似的。在语言中频率总是无视规范化。并不是所有不规则形式都是异干互补的产物:man/men, tooth/teeth, do/does也需要单独研究,但是它们中没一个属于异干互补。
我们已经扫视完了这个纠结的问题,最后也没搞清楚,但这恰是源于重建而非直接记录的所有事物的命运。不管怎样,我已经解答了一个古老问题,且问心无愧。
转译自:http://blog.oup.com/2013/01/why-is-the-past-tense-of-go-went-suppletion/
版权所有 2011-2015 北京云英一语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Y-English All Rights Reserve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华清嘉园商务会馆802
电话:400-876-3898 010-82863898 82863899 传真:010-82863897